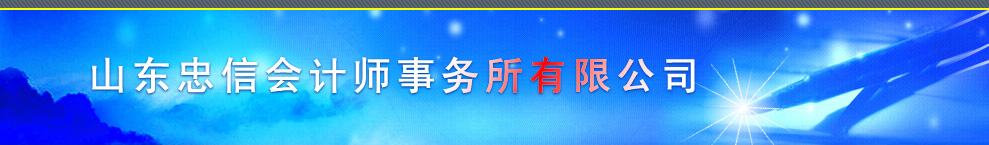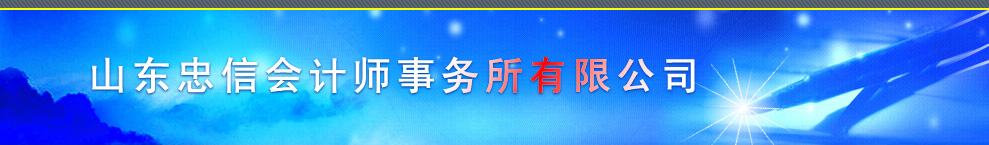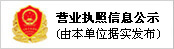位置:山东忠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> 荟萃拾零
孙长江细说“真理”一文刊发幕后
【来自:大众日报 点击数:1346 更新:2008/5/19 10:06:50
】
30年前的5月10日,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发表,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。
这场大讨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,澄清了思想是非、理论是非,驳倒了“两个凡是”,实现了拨乱反正,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,从而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序幕。
1978年5月10日,由中央党校主办的《理论动态》发表了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一文,第二天《光明日报》以特约评论员署名全文发表,新华社发了通稿。5月12日,《人民日报》、《解放军报》全文转载,此后,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党报、党刊竞相转载,从而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。
当年在中央党校直接参与撰写、修改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一文的孙长江,如今已是75岁的古稀老人。回首“真理”回归的岁月,孙长江感慨万千地说:一切仍历历在目,仿佛就在昨天。
创办《理论动态》
胡耀邦到中央党校后不久,就找吴江谈话说,党校也需要有自己的刊物,没有一个阵地不行,提出要创办一个“理论性的刊物”。
1977年4月间,由毛著编辑委员会编纂的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五卷出版发行。5月1日,华国锋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为《毛选》第五卷出版而作的署名文章《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》,文章指出: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后,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”的主要任务仍然是抓“党内走资派”,“继续革命”就是“继续反右”等等。该文发表后,全党组织学习,中央党校自然也不例外。
7月12日,胡耀邦召集中央党校各教研室的部分同志座谈。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在会上发言,他讲了三点意见:一是不能将“文革的重点是整走资派”这一提法扩大为“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重要对象是整走资派”;二是“继续革命”的任务包括经济基础方面的革新和技术革命,即生产力方面的革命;三是有人认为“不断革命”就是“不断反右”,这不是毛泽东思想,毛主席说“既要反对左,也要反对右”。
当天晚上,胡耀邦就找吴江谈话说:“我们的刊物可以办了,你将今天的发言整理成一篇短文,字数不超过五千,明天交稿,作为创刊号的文章发表。刊物的名称我已经想好了,就叫《理论动态》吧!每五天出一期,一期只登一篇文章。”
就这样,《理论动态》创刊号于1977年7月15日作为粉碎“四人帮”后的党内第一个理论刊物出版。创刊号所刊登的就是吴江同志撰写的《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》,发行范围是中央和中央各部委以及各省市负责人,中央党校学员人手一册。
为了办好《理论动态》,胡耀邦让吴江组织了一个班子,在理论研究室成立三个组即:理论组、动态组、外文资料组。孙长江是理论组组长,《理论动态》的编辑主要由动态组负责。孙长江说,胡耀邦对这份刊物寄予厚望,他经常是亲自定调子、出题目,并亲自修改定稿,为刊物“找米下锅”。
起草初稿
孙长江说,当时他在理论组。一天,吴江主任对他说,耀邦最近有个讲话,讲到研究党史要坚守两个原则:一是要准确完整地运用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;二是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、辨别一切是非的标准,包括路线是非在内。党史研究室的同志写了个东西,耀邦不满意,党校有的学员也有误解,认为检验真理一个要看实践,一个要看毛泽东思想。孙长江听了说:“这个不行,容易出问题,如果实践与毛泽东思想发生矛盾怎么办呢?”
吴江与孙长江就这个问题谈了很久,两个人取得了一个共识就是:检验真理不能有两个标准,只能有一个标准。最后他们商定,由孙长江起草写一篇文章,题目就叫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。
就在孙长江在家中起草文章的时候,正巧遇到人民大学的一个老同事来串门,她看到孙长江在家中撰写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这篇文章,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《光明日报》的总编辑杨西光(这个同志是杨西光的老部下)。后来,她再次见到孙长江时说:“我告诉《光明日报》的杨西光了,你在起草一个真理标准的文章。”
文章写了个初稿,大约有6000多字,孙长江交给了吴江,吴江看了后感觉不是十分满意。这个文章的初稿孙长江也给同事孟凡(资料组组长)、王聚武(动态组组长)、沈宝祥(时任动态组成员)看过。
集体智慧
杨西光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复校后的第一期高中级干部读书班学习。听了胡耀邦同志的一个讲话,他很受启发,就安排报社找一找有没有“关于真理标准”的稿子。此前,报社的同志已经向南京大学的讲师胡福明约了一篇“关于真理标准”的稿子,正准备安排在《光明日报》哲学版。杨西光看了后,要求将该文从哲学版上撤下来,准备作为重点文章另发。他认为文章还需要进一步修改,恰在这时他得知中央党校的孙长江也在撰写这篇文章。于是就安排秘书陶凯联系孙长江,陶凯把电话打到党校对孙长江说:“有篇文章,西光同志想请你帮忙看一下,《光明日报》准备发表。”
其后,《光明日报》的编辑王强华同志就将报社修改过多次的《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》文章小样送到孙长江的家中。
孙长江仔细看了胡福明写的文章,感觉哲理性不强,他又把文章给同事沈宝祥看了,沈认为这个题目不好,“一切真理”在逻辑上不通。在修改过程中,他又与《光明日报》的同志在一起讨论了几次。这时,杨西光又找到吴江,说了这篇稿子的情况,他对吴江说,想请孙长江同志修改后先在《理论动态》发一下,并且说他已经请示了耀邦。
吴江这才知道孙长江正在修改《光明日报》送来的稿子,他对孙长江说:“作者能写出这个题目还是有点勇气的!”然后又说:“你看看,尽量把你写的和这篇文章捏在一起,保留好的东西,题目还用我们原来的。”
就这样,孙长江根据吴江的要求继续修改这篇文章,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,他还特意找来了自己的学生和朋友——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王贵秀、张显扬、董新民,对他们说:“你们是搞理论的,请你们一块来商量商量。”他们三人都是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的,与孙长江有师生之谊,于是三个人就跑到孙长江的家中一块讨论这篇文章。
几个人在一起讨论了好多次,在讨论中大家畅所欲言,各抒己见,有时会为一个问题而争执起来。他们讨论文章,孙长江的爱人孙伟就下厨做菜,讨论结束后几个人小酌一番,又边吃边讨论。如今,已经退休的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,回忆起这段往事仍然记忆犹新。
提及文章的撰写和修改过程,孙长江说:文章中的“唯一”二字非常重要。这也是他与吴江同志共同的观点,吴江认为“唯一”二字采自列宁。
孙长江将改完的稿子交给吴江,吴江又对稿子稍作修改,并于4月27日签署了处理意见:孟凡同志:请即排印15份,送胡、杨、作者各一份(航空发出),五月十日那期用。吴江四月二十七日。
其后,《理论动态》的同志又将此稿打出清样让耀邦同志审阅了两次。1978年5月8日送到印刷厂正式印刷。
受人指责
1978年5月10日,《理论动态》第60期全文刊发了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。
第二天,《光明日报》以“特约评论员”的署名发表。“特约评论员”的署名是胡耀邦同志的要求。这是胡耀邦同志的一个创造。这个署名的使用有一个过程。最初提出这个署名,是《人民日报》要发表《理论动态》的一篇文章,来电话问怎么署名。“动态组”的同志请示胡耀邦,胡耀邦说“报纸发文章,写评论,有些问题大家都可以评论嘛!报纸要走群众路线嘛!我们可以参加评论嘛!我们也可以当特约评论员嘛!”秘书陈维仁把耀邦同志这个意见电话告知了《人民日报》。此后《人民日报》、《光明日报》发表《理论动态》文章时均使用“特约评论员”这个署名。“真理”一文以特约评论员之名在《光明日报》刊出,意味着胡耀邦同志对这篇文章承担着全部的政治责任。
《光明日报》以“特约评论员”的署名发表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的第二天,《人民日报》、《解放军报》全文转载。就在《人民日报》转发“真理”一文的当天晚上,即5月12日晚,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五卷编辑办公室(简称“毛办”)的吴冷西就打电话给《人民日报》总编辑胡绩伟,提出严厉的指责,说这篇文章是“砍旗”、“犯了方向性错误”、“政治上问题很大、很坏很坏”等等。
紧接着,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汪东兴在6月15日召开的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紧急会议上,又对“真理”一文进行了严厉的批判。他指责“特约评论员”说:“特约,是谁嘛?不知道,这些‘特约评论员’有问题”。他特别对《人民日报》施加压力,说《人民日报》“没有党性”、“没把好关”。
历史的潮流总是滚滚向前,冰雪毕竟挡不住春天的脚步。“真理”一文发表后,全国各大报纸争相转载,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由此而展开。
再写姊妹篇
孙长江说,“真理”一文之所以产生这么大的反响,“功劳”应在吴冷西,要不是他批评也不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。就在吴冷西打电话指责《人民日报》总编辑胡绩伟的第二天,胡绩伟就给孙长江打电话说:“吴冷西打电话严厉批评我了”,同时他也打电话告知了吴江。听了胡绩伟所说的情况,孙长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,当晚他就匆忙跑到吴江家里商量对策。他对吴江说:“我们赶紧写文章批驳吴冷西的意见,不然等我们被打倒后就没有发言权了。”吴江同意孙长江的观点说:“赶紧弄!”于是,在吴江同志的主持下,孙长江很快写就了《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》一文的初稿,吴江在初稿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撰写和修改,定稿后送给胡耀邦,胡耀邦看了之后,让秘书张耀光回了个电话:“三个月以后再说”,意思是让冷一冷再说。从这个细节看出来,耀邦同志面对的压力很大,孙长江说,这种压力主要是来自汪东兴和华国锋。
看到文章发表的机会不大了,吴江索性放开手又将稿子作了三次修改。恰在这时,《解放军报》的副总编姚远方到吴江家里做客,他与吴江同志是延安鲁艺的同学。与此同时,正赶上《解放军报》6月2日发表了《邓副主席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》全文,并且还特意在报眼位置刊登了讲话内容的摘要: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,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,这是毫无疑义的,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,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,解决实际问题,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,这是一切共产党员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、工作方法。实事求是,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、根本点。这是唯物主义。
过了几天,姚远方就告诉吴江说:“华楠总编辑说文章可以用,文章的思想内容与邓小平讲话的精神是一致的。”文章出来清样后,吴江提醒姚远方说:“是否请罗瑞卿总长看看。”
于是,《解放军报》又将稿子转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,罗看后提出了两条意见:一是把《实践论》的思想多引一点;二是把邓小平报告的内容再加一点。
文章发表之前,吴江同志用检讨的口气向胡耀邦汇报说:“我们没有请示您,把这篇文章送到了《解放军报》,《解放军报》说要刊发。”胡耀邦说:“我知道了,罗总长已与我通电话了。”
《解放军报》在发表该文时接受了吴江建议,不用个人署名,以《解放军报》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。
6月24日,《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》在《解放军报》以《解放军报》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全文发表。全文17000字,在《解放军报》占用了第一版的大半个版,第二版的整版,第三版的一部分。这也是《解放军报》第一次用《解放军报》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文章。当天《人民日报》、《光明日报》均以同样的署名全文发表。
孙长江说,这篇文章是“真理”一文的姊妹篇,其影响力甚至比第一篇文章还要大。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对“真理”标准讨论的有力支持和推动,同时也促使了第二篇文章即《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》以更高的水平写成和刊发。关于第二篇文章的历史贡献,沈宝祥教授在《胡耀邦与真理标准讨论》一书中援引原《人民日报》社长李庄同志的话说:“这篇文章引起轰动效应,相当彻底地解开了绝大多数怀疑论者和不理解者的思想疙瘩,令‘凡是’论者不能应战。”
无怨无悔
孙长江在中央党校一直工作了五年,1983年夏天,他被调到首都师范大学继续从事教学生涯直至离休。真理标准讨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,澄清了思想是非、理论是非,驳倒了“两个凡是”,实现了拨乱反正,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,从而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序幕。
三十年岁月沧桑,三十年真理永存。当年的“真理”战士们有的已经作古,健在的也都已年逾古稀,他们的“带头大哥”——中央党校原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如今已是91岁高龄的耄耋老人。孙长江说,由于年龄原因,他们已不能经常见面,但还时常互致电话问候。谈起“真理”与“两个凡是”那场斗争,孙长江说,自己有幸成为了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者,时代总是向前发展的,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和今天我们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再一次证明: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看着眼前这位年过古稀,却依然个性张扬的思想者,我不禁想起一句歌词:你是英雄,就注定无怨无悔!
(作者单位:中共中央党校)
■相关链接
从哲学之路到理论战士
□程冠军
身材魁梧的孙长江看上去很像一个北方大汉,其实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南方人。1933年1月15日孙长江生于福建厦门,5岁那年,由于家庭的变故,他一个人跟随母亲到泉州生活。母亲是个小学教员,靠微薄的薪水养家并供孙长江读完了小学和初中,1949年9月正在读高中二年级的孙长江报名参加了解放军,跟随部队到福建永安剿匪。1952年,他从部队被选调为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历史系。谈到自己所学的历史专业,孙长江说,他自幼就不喜欢数学,同时也不喜欢外语,于是就挑选了一个不学外语和数理化的中国史专业。
青年时代的孙长江就善于独立思考而且思想解放,1955年他的大学毕业论文就是《论谭嗣同》。毕业后,他被留校任教,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教学和研究。“文革”期间,他被下放到江西省余江县劳动。
1973年,孙长江回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工作。1974年,他被调到了国务院科教组(教育部的前身),在《教育革命通讯》(《人民教育》的前身)当了一名编辑。当时科教组的负责人是周恩来的秘书李琦,编辑部负责人是龚育之。
在科教组工作期间,他与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当时,毛泽东提出要找一个搞马列主义的中青年学者给冯友兰当助手,协助冯编写《中国哲学史》,这时,与孙长江要好的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汤一介列了一个名单,孙长江名列其中。当组织找他谈话时,他表示不愿意去,因为他考虑到冯友兰是哲学权威,自己怕难以胜任。最后,只好定下来每周去冯的家中两次。
孙长江说,在他的印象中,冯友兰留着长长的胡子,是一个很有大家风范的学者。接触了一两次,冯友兰就开始喜欢上了他这个有个性的青年助手。
那时的冯友兰被当做资产阶级的白旗,正在写检讨,有一次他把写好的检讨让孙长江提意见,孙长江看了检讨中有这样一句话“我是全国最大的一个尊孔派”,他就对冯友兰说:“不要这样写,您怎么能这样说呢?还有比您更大的呢?”冯友兰认为孙长江说得有道理,于是就接受建议将这句话改为“像我这样一个尊孔派”。
孙长江说,在给冯当助手之前,他作为一个“革命”青年,竟然经常与汤一介一起在报上发表文章批判冯友兰的观点,为了使文章有力度,还时常生搬硬套一些马列理论,现在想来真是十分滑稽。他说,冯友兰是中国真正的哲学家,与冯友兰的这段交往,使他获益匪浅。
1977年4月胡耀邦同志任中央党校副校长,主持党校工作。胡耀邦到任后,首先开展了两项重要工作:一是组织揭批“四人帮”;二是组建党校的行政机构和各教研室。这时,在中央党校一直出于赋闲状态的吴江,进入了胡耀邦的视野,在组建教研室时被任命为理论研究主任。
1978年初,吴江找孙长江谈话,提出要调他到中央党校。因为吴江既是孙长江的老师又是老上级,孙长江便欣然同意去了中央党校——这块党的重要的思想理论阵地。正是这一次选择,使得他由哲学之路走上了理论之路,成为了思想解放运动中的一名战士。